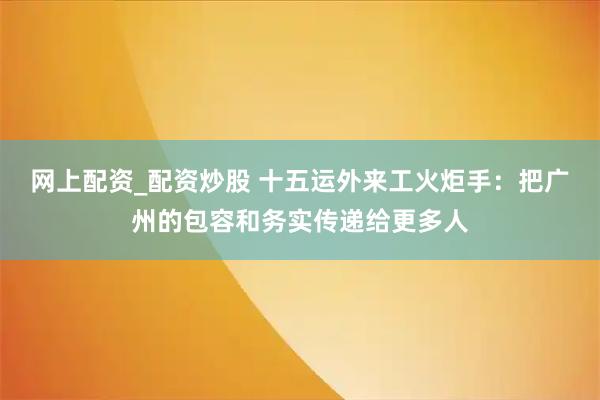“五月底的电报到了?徐向前真要去山东挂帅?”1940年5月31日网上配资_配资炒股,枣园一间窑洞里的警卫员探头问话,砖红色的油灯晃了一下。朱德抬眼,只回了两个字:“是的。”短短对话,却在军中炸开了锅——向来把官职当身外物的徐向前,为何突然改了脾性?

徐在红军时期留下的印象是“退一步、心里稳”,换成今天的话就是从不抢镜头。鄂豫皖根据地创立时,他曾三让师长;长征前夕,被推举为四方面军总指挥,他也“先推刘伯承”。这份低调,甚至让不少老兵以为他天生排斥权力。偏偏1940年,他主动给中央发电报,点名“接115师,陈光为副,罗荣桓为政委”。用朱德的话说,这像一头温顺的骆驼忽然加鞭,肯定有因。
原因得从山东讲起。1939年底,115师与山东纵队在沂蒙山区“同住不同炕”。两套番号,各有山头,表面礼让,暗中别苗头。山东纵队路线灵活,却缺重武器;115师装备整齐,却对地形生疏。日军一个据点能挤进两拨八路军侦察员,互相还以为对方是敌特,这不是笑话,是浪费。

更棘手的是战略分歧。陈光强调会战,主张集中打痛一两个据点;黎玉强调游击,提议处处点火拉大面。双方开会往往拍桌子。有人记下当时场面:“一张作战地图,被两种颜色的铅笔画得像花脸。”指挥分裂的结果,是日军“囚笼政策”迅速得手。短短几个月,山东境内碉堡增长到700座以上,铁道、公路被严密封锁,八路军机动空间日益被挤压。
徐向前接到前方情报后发现,要冲破笼子,必须把“攻坚拳头”和“群众网络”合在一起。他计算过兵力:115师七千多人,一昼夜能突破一条封锁线;山东纵队两万余人,布满村镇。二者若脱节,日军随时能“分片清剿”。解决之道只有一个——把指挥链缩短为一条。于是,一道自荐电报飞往延安,他甚至在末尾加注“战后即辞”。

有人怀疑他是为四方面军旧部争地盘,这种猜测在四川老兵中流传不止。可徐向前的思路明白:115师特长是集团突击,山纵的长项是地方武装发动,两者互补。拿下泰西交通线后,115师可就地“地方化”,山纵可抽调精干练主力。一旦成型,山东抗战的格局会出现合力攻坚、遍地支点的新局面。为了这个目标,师长头衔只是一张“通行证”。

进鲁途中,他从晋冀交界处坠马,腰椎骨折,被迫停下。担架上,徐把手绘的《鲁南交通节点图》交给罗荣桓,说了一句:“图上七口子,把住就行。”短句无悲情,却分量极重。三个月后,罗荣桓在费县以南依图设伏,击毁日军装甲车九辆,活捉少佐井上久仁。山东纵队由此赢得喘息,115师也趁机在梁山一役打开缺口。
无法亲临前线的徐向前被送回延安疗伤。中央随后决定调整山东军政委员会,罗荣桓兼书记,陈光任副,总指挥权归军区。新的指挥格局与徐最初的设想相差无几。山东根据地由此实现了“主力统一—地方协同”的模式,日军在鲁中的道路虽仍存在,却再没形成闭合网。

1955年授衔仪式上,他只说了一句话:“山东的功劳,大半在罗荣桓。”语气平常,但不争之名、敢争之责的轮廓已呈现。当年主动请缨,不是改性子,更不是恋权,而是在“战局需要”与“个人淡泊”之间,他毫不犹豫地选了前者——简单,却锋利。
联合证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